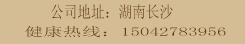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蚕 > 蚕的种类 > 传承创新楚韵荆州凤飞龙腾织锦绣神
当前位置: 蚕 > 蚕的种类 > 传承创新楚韵荆州凤飞龙腾织锦绣神

![]() 当前位置: 蚕 > 蚕的种类 > 传承创新楚韵荆州凤飞龙腾织锦绣神
当前位置: 蚕 > 蚕的种类 > 传承创新楚韵荆州凤飞龙腾织锦绣神
编者按
“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乎照万方。”让大诗人屈原不吝溢美之词,让古代罗马皇帝视为珍宝,让古代服饰研究泰斗沈从文热泪盈眶、拜伏在地;在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千年古堡中,在风景优美的地中海沿岸的历史遗迹里,甚至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游牧民族的墓葬里,都有它华美的身影——东方瑰宝楚国丝绸。
从马山一号墓开启的那一刻,就是沉埋在历史角落的楚文化涅槃之日。楚国丝绸,用绝世风采为楚文化披上一袭华贵神秘、充满魔力的锦袍,从文化、艺术与物质的角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文化骚雅狂放、心游万仞、彪炳千秋的魅力,为楚文化研究的正源清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一件件让世界为之惊叹、即便运用现代科技也很难复制的丝绸制品,承载着楚文化绚烂、雄奇、瑰丽、博大、进取的丰厚内涵,让我们在感受楚人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亲历楚人在现实生活中展现的高雅审美趣味和奔放不羁的热情,直面楚人狂放、自由生命的凤凰涅槃。
楚国丝绸提炼整合当时 的丝织工艺,把文明的精髓纳入一针一线之间,以 水准把生活的日常升华为艺术的圭臬,超越时代认知的精湛工艺和浪漫严谨的纹饰,清晰勾画出历史和文化的脉络,诉说着年楚国的强盛和繁华,再现了当年楚国综合实力最辉煌的高光时刻。
举世无匹的艺术造型和想象,成为无数当代艺术家创作的素材和灵感的宝库,艺术由此获得新生。正是它的存在,让我们愈发自信,在这块拥有非凡创造力的土地上,我们有能力、有信心继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知荆州、爱荆州、兴荆州。传承历史,展望未来,文化自信助推城市发展。本期“文化荆州”特聘请楚文化研究学者、荆州市社科联学术委员张卫平先生爬梳剔抉、挥笔成文,穿越年岁月悠悠的时光烟尘,梳理楚天之上灵动的彩虹的前世今生,于绢、绨、纱、罗、绮、锦、绦的经纬纵横中,发掘楚国丝绸超越时代的精湛工艺和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擦亮这颗楚文化*上的耀眼明珠。
楚文化*上的耀眼明珠
——漫谈楚国丝绸的前世今生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古丝绸一直“躲藏”在文献古籍之中,仅仅只是在零星的考古发掘中闪现华丽高贵的身影。直到年,荆州马山战国丝绸的横空出世,才让楚国丝绸的绝世风采穿越多年的历史烟尘,真实、灵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几乎包括了东周时期中国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是我国考古史上对东周丝织品的一次最为集中的重大发现。这些织造精良、绣纹绚丽、色彩鲜艳的楚国丝绸,犹如艺术殿堂中一朵朵争奇斗艳的奇葩,向世人展示着独特的光辉。
荆州马山一号楚墓的惊世发现,让世界瞠目!人们从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丝绸宝库”中,看到了楚人在多年前织造出连今人用高科技都难以复制出来的丝织物;人们这才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丝织生产确如文献记载的那样,以一枝独秀引领着当时中国时尚前沿,并沿着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
震惊世界的马山战国丝绸,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写了中国古代史。过去,楚文化曾一度被认为是失败的、落后的文化,由于荆州马山“战国丝绸宝库”的问世,“彻底改变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刘玉堂、张硕《长江流域服饰文化》)”。年,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参观了荆州博物馆的楚汉丝绸后,受到极大的震撼,认为中国历史要因灿烂的楚文化而改写,并一再说,“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以与同期的*河文化并驾齐驱”。
丝绸
古代重要的战略物资
楚墓出土的丝绸花卉图案
在古代,丝绸地位与今天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完全可以相提并论。战略物资,是二战前期形成的概念,是指对国计民生和国防具有重要作用的物资资料。
湖北、湖南楚墓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荆州马山一号楚墓、荆门包山大冢、随州曾侯乙墓以及70年代被誉为承袭荆风楚韵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和荆州纪南城凤凰山、号汉墓的重大考古新发现,充分证明了战国中晚期楚国纺织业已进入鼎盛阶段。也就是说,在那个丝织物稀有的时代,楚国织造就完全能够满足需求。
楚国丝绸的辉煌发展,与战争紧紧相连。通过战争,“山寨”别国高端丝绸,是“楚国织造”创新发展的起点。最初,楚国丝绸生产与青铜兵器铸造一样,其技术水平始终在低端徘徊。当时,鲁国丝织技术则非常先进,织造之美让楚国国君非常眼馋。为了得到鲁国丝织技术,楚王不惜重兵压境、武力威胁,硬是逼着鲁国用数以百计熟练纺织技工换取一时和平,从而掘到了发展丝织业的“ 桶金”。正如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凤春研究员所说,“楚人在对外的扩张中,似乎也是不遗余力地谋求发展本国的纺织业,无论是资源,还是技术都尽为己有”。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那年楚国大兵压境直逼鲁国阳桥,鲁成公看出了楚国锋芒所指,便在无奈中送上非常优厚的“讲和条件”——献上百多名纺织丝绸的技工,楚国得到梦寐以求的织造工匠后才退了兵。“毫无疑问,鲁国这些能工巧匠对楚国纺织业发展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后来,楚国干脆灭了鲁国,让鲁国先进的丝织技术为“楚国织造”发扬光大。这类以战略资源或技术人才为争夺对象的战事,在楚国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
创新,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人才,二是原材料。楚国得到技术人才后,又将目光盯住了原材料——桑树和桑叶。历史记载,“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从而诱发了吴楚间声势浩大、血流成河的战争。战争的导火索就是因为吴、楚两国的妇女儿童在边境线上争夺桑叶。结果,导致楚国灭了卑梁(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吴国攻占了钟离(今安徽天长县西北)。因为采摘桑叶这种夹不上筷子的小事儿而导致两国一场惨烈战争,可见,丝绸在那时已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战略物资和必需品。
后来,楚国将鲁地先进技术与工艺逐步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使丝织业迅速发展成为楚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并成为楚文化一大支柱和特色。接着,楚国又先后灭了吴、越两国,将吴越植桑、养蚕、织丝先进技术与工艺推广到楚国全境。楚国在先后灭了鲁国、吴国、越国后,将四国技术与工艺交融发展,使楚国丝绸织品后来居上,超过齐鲁,跻身中国丝绸产业 方阵。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陈振裕先生说,“马山一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齐全,花纹美观,色彩艳丽,是我国先秦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最重要的发现,被誉为楚国的‘丝绸宝库’。这批丝织品,主要是楚地的产品,表明当时楚国已经掌握了饲蚕、缫丝、织造和练染等整套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不仅仅是古文献,人们饲蚕、缫丝、织造的场景在唐诗中也有突出的展现。正如唐代诗人李白这首《荆州歌》中所描写的那样,五月的荆州大地,麦子熟了,蚕蛹化茧,蚕蛾破茧而出,姑娘们在缲丝中思绪随着飞蛾飞向夫君,思念之情多得超过了满天舞动的蚕丝。
丝绸作为古代战略物资,有着与*金一样的硬通货价值。于是,丝绸便与粮食一样,成为朝廷支付官吏俸禄的“货币”。古人在丝绸的流通中,发明了“匹”这个度量单位。这在凤凰山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也得到了证实。而大文豪郭沫若则在《奴隶制时代》一文里说,“五名奴隶等于一匹马加一束丝”。可见蚕丝之珍贵。
特别有意思的是,曾经为争夺桑蚕资源和丝织技术工匠而悍然发动战争的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出口的丝绸居然会在遥远的西方诱发战争。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国之间为了争夺中国丝绸贸易的垄断权,竟然兵戎相见,打了整整20年的“丝绢之战”。可见,当时在欧洲丝绸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
“事*神”
古代丝绸发展原动力
对龙对凤纹中的龙纹
中国的丝绸业,从起步之初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早期的丝绸,因为弥足珍贵,刚一诞生就成为了祭祀用品,这也与青铜器和玉器一样,有着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于是,有专家说,中国丝绸业一开始可能就是一项宗教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
据《礼记·礼运》记载,“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神上帝,皆从其朔”。治麻以得布,布以养生;治丝以得帛,帛以送死。这里已对布与帛的功用有所区分,布用于生前服饰,而帛主要用于尸服。蚕桑丝绸,在发明之初就有着“事*神而用之”的含义,直到商周时期仍然普遍用于祭祀。后来,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提高、思想解放以及等级观念松懈,丝绸的使用才变得逐渐普及起来。对此,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先生根据对大量史料和考古发掘出土实物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桑蚕丝绸业起源的契机在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他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的先氏,通过观察蚕自卵至蛹并化飞蛾飞翔的生态变化,将蚕与人的生死、死后升天相联系。“于是,蚕成了沟通生与死、天与地的引路神,桑树成为羽化升天的工具”“因此,桑丝的利用,最初的目的是事*神”。
于是,人们从考古发现中看到中国古人最开始使用的丝绸,就是在祭礼中用来包裹礼器与尸体。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众多出土文物上得到验证,而从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更是得到证实。马山楚墓中的尸骨,就是用9根锦带捆扎并用13层丝绸衣衾紧紧裹成一个衣衾包裹。年10月,考古发掘的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棺上盖了四床做工精细、稀有罕见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帏,如此完整的多床荒帏的出土,在全国尚属首次,被誉为出土“棺罩之最”。可见,中国的丝绸业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上古时期人类最为重要的两项活动——生存与繁衍,都是在桑林中进行的。那时,为了子孙后代的繁衍,古人们都是到桑林里去求子。《小雅·隰桑》中说:“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那时,男女幽会一般都在桑林这个非常特别的场所里。桑树被古人臆想成为神树“扶桑”——太阳栖息之地。在先秦的典籍里,对扶桑的解释为“神木名,传说日出其下”,扶桑总是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而出现。其实,所谓扶桑,就是古老的植物崇拜,以桑树为原型创造的神树,如同印度的神树菩提树一般。
如今,我们从楚地的出土文物中得到了证实。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出土一幅楚国帛画中,上方绘有一轮红日,火红的太阳中站立着一只金鸟,红日下方,有两条龙飞舞于扶桑神树和九个太阳之间。画中高大的神树枝条绵长柔韧,叶形极似桑叶。可见,这株桑树充当着神话中天界里不可或缺的角色。对此,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先生说:“我们的祖先从对蚕的崇拜中衍生出了对桑树的崇拜,求子、求雨等重大活动均在桑林中进行,进而产生了扶桑树的概念,成为天地间沟通的渠道之一。”蚕的变化如此神奇,桑树就更加神圣了,从而使古老的丝绸拥有其它纺织品无法比拟的神圣意义。
当然,丝绸“事*神”,并非仅仅是用丝绸包裹礼器与尸体,还用丝绸做成招*的“*幡”。就说楚怀王客死他乡吧,消息传回纪南城后,屈原一边舞动着手中用丝织物做成的*幡,一边吟唱着“*兮归来!哀江南!”深情地召唤着楚怀王的*魄能从西北秦国返回故里。他手中舞动的、用于招*的“*幡”,就是源于楚人创造的“招*复魄”“*归天为神”的转换法器——绣幡。年,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就从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里出土了一件“招*”的绣幡。绣幡呈长方形,顶端中间有一丝环,中部以红褐色绢为地,刺绣金*、靛蓝色变形龙凤缠枝花卉,周缘为褐红色连续动物纹及菱形纹锦,出土时铺于棺盖之上。
改写历史,楚国丝绸
出色的创造与发明
凤斗龙虎纹
“先秦的丝织品和丝绣品,迄今已发现的完整实物,一概出自楚墓。”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认为,楚文化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 代表性的文化,是二元耦合格局的华夏文化中的一元。
“湖北一带的蚕织业的兴起和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兴盛密切相关。楚国统治者一直非常重视发展蚕织生产。”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楚国丝织工艺和丝绣工艺都是妙绝一世的珍品。为了说明以上论点,荆州博物馆的滕壬生先生运用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进行说明,比如,从河南信阳楚墓出土过类似绮的丝织品;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过缯、帛画等丝织品;长沙左家塘出土衣衾残片,广济桥出土绢袋、丝带和织锦,烈士公园墓出土龙凤纹刺绣;荆州望山楚墓出土绢、绣和提花丝帛,雨台山楚墓出土绢和绦带,九店砖瓦厂楚墓出土丝织、刺绣物;荆门包山楚墓出土锦、绮、绢、纱。特别是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保存完好的丝织物35件及锦、纱、绣、锦等丝绸碎片片。如此众多的丝织和刺绣物品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楚国纺织、刺绣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专家认为,楚国的丝织品有着织造复杂、颜色艳丽、花纹繁缛、富于变化的特色。于是,我们从荆州楚墓出土的丝绸中看到,纹饰排列组合既灵活多变,又富丽多姿。纹饰以几何纹为主体,再加上珍禽异兽纹和人物行为纹。有些用绢和素罗作绣地的织品,用多种色彩丝线手工刺绣出花纹。这些刺绣的纹饰,以龙凤纹为主体,并间以植物,使得刺绣纹饰更富有立体感,图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将楚人奇诡的民族信仰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充分地展现在服料上。正如*凤春研究员所说,“楚人正是因拥有这些织品,再加以精工巧裁,形成了一道与诸夏迥异的服装风景线”。
锦,是楚国丝绸最富特色的种类之一。马山楚墓出土的锦的种类繁多,二色锦有塔形锦等6种,三色锦有舞人、动物、纹锦等3种。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横贯全幅,织造时使用个提花综,充分反映当时已有相当先进的提花织机和娴熟的织造技术。马山楚墓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锦面,是目前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 的锦。在古代,中国先进纺机一直让西方刮目相看。在看到荆州出土的夹袱锦面以前,有些西方学者是否认中国古代有提花机的,而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则说,“马山出土的复杂组织结构的大提花织物锦的出现,证实了战国时期织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对此,《中国文物报》原总编辑朱启新说得更加具体,“这幅锦共用经线根,在世界纺织史上也是非常出色的创造与发明。”
刺绣,代表着楚国丝绸的 水平。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断定,表明楚国在丝织、刺绣方面已走在东周列国的前列。荆州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石”字菱纹锦绣镜衣,将我国锦上刺绣的历史提前了多年。楚绣虽然针法比较单一,但花纹各不相同,锁扣十分均匀、整齐、线条流畅,较多地运用改变线条方向、排列方式、稀疏密度的方法来表现各种禽兽的细部,突破了单调、呆板的传统,给人以生动、多变之感。刺绣纹样的构图讲究对称平衡,动静结合,色彩搭配适当,内容充满神话色彩,鲜明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对后世刺绣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绨、组、绦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丝绸新品种。《禹贡》里说,“荆州,包匦菁茅,厥篚玄纁玑组。”《左传》也云,鲁襄公三年(公元前年),楚子重伐吴,“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这种组带,在马山一号楚墓中就土了10件,主要用于衣领、缘和囊、帽及捆扎双臂等用,不断印证了古文献的记载,还充分证明了编组带是楚国地区的传统工艺产品。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针织绦是战国丝织技术的重要创新,结构复杂,编织方法巧妙,把我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特别令人震惊与不可思议的,是针织绦纹饰的精细。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到针织绦的纹饰,只有通过显微镜放大后才能看清。那些巧夺天工的纹饰,就像是姑娘头上梳的辫子,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股“辫子”,竟然都由上千股丝组合编织而成。
马山考古新发现
开启丝绸起源新思路
马山一号墓出土服饰的复原效果图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丝织业空前发展与繁荣的时期。只是,文史资料显示,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是中原之地,史有“齐纨鲁缡”“冠带衣履天下”之说。
从《禹贡》《诗经》等古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生产主要集中在*河流域的北方地区,而在长江流域仅仅只在荆州、扬州和徐州部分地区略有出产。因此,长期以来,历代史学家都认为,*河流域是中国丝织物中心产区,长江流域仅仅只有低水平的零量丝织物生产。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先秦时期丝织品实物,几乎都发生在历史上楚国的核心地区,于是考古学便开始不断地挑战文献学。
其实,*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蚕桑丝织的主要起源地。专家认为,长江中游的楚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纺织业就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丝织物的起源有一个非常有力的重要物证——纺轮。从距今年左右屈家岭文化出土的、现藏于荆州博物馆的大量彩陶纺轮,足以证实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原始纺织的发展。这些陶纺轮,大都为泥质陶,少量夹细砂陶,陶色有灰、黑、红、*等色。对此,刘兴林、范全民在《长江流域丝绸文化》中写道:“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纺轮数量巨大、型式多样、纹饰复杂,揭示了该地区原始纺织手工业的繁荣和发达,同时也凸显出这里原始纺织文化的一大特色。”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刘玉堂进一步指出,“纺轮可以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纺线工具,是现代纺织业里广泛使用的纺绽的鼻祖。仅从彩陶纺轮的装饰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原始纺织业的进步与发达。而精心彩绘、充满艺术气息的彩绘纺轮,似乎也昭示长江文明浪漫放达的先声。”
年以来,先后从江陵九店、江陵望山楚墓、江陵藤店楚墓、荆州天星观楚墓以及荆门包山楚墓、随州曾侯乙墓和一批西汉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实物后,充分证明了先秦时期的荆州就是中国长江流域的丝织品生产中心。
特别有意思的是,国外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楚国织造”的存在。上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巴泽雷克古墓中发现的刺绣丝织物,无论丝纤维、花纹风格还是丝织工艺,都与楚国丝织物有着惊人的一致!中俄学者一致认为,这些丝织品是从楚国传到中亚地区的。清华大学教授*能馥先生说,“在俄罗斯巴泽雷克的公元前五世纪古墓出土的刺绣鞍褥面,其图案形象与湖北江陵及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刺绣图案风格完全一致”。对此,荆州博物馆研究馆员彭浩先生也说,“值得注意的是,巴泽雷克第6号墓出土有一面四‘山’纹铜镜,在阿尔泰山西麓也发现过一面相同花纹的铜镜。这种铜镜原产于楚国,流行于战国晚期至秦代”。彭浩先生告诉我说,“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丝绸外传的最早实例”。考古专家认为,在俄罗斯和德国“发现的战国织绣,令今人触摸到中国丝绸强大的生命力及其对世界的震撼”。
考古发现,楚国织造的丝绸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出口”到了欧洲。可见,当时楚国已经拥有世界上 的纺织技术与工艺。考古人员还在长沙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方“中织室玺”铜印。有学者认为,“中织室玺”铜印“为掌管宫廷纺织事业官吏所用之印”,而“识室应是掌管王室丝帛织造的官府机构”,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楚国织绣的发达。
西汉刘向的《管子·小匡篇》中说,楚能“贡丝于周室,绝无夸耀粉饰之辞”。楚国的始封君熊绎“筚路蓝缕”,在创业之初坐的是柴车,穿的是破衣烂衫,虽然楚国建国之初的丝织业水平也许落后于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不断扩张与崛起,特别是采取“拿来主义”,整合了多国先进技术的,楚人后来居上,用先进的技术与工艺生产的丝织品,成为向周王朝纳贡的上品。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凤春说:“仅丝织而言,此时楚国已是后来居上了。”
荆州市先后从九店、望山、马山、雨台山等地楚墓和凤凰山、谢家桥西汉墓出土了大批丝织物品,颠覆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的结论,充分证明楚国丝织业在战国中晚期已经进入了鼎盛阶段,并成为中国丝织物的中心产区。这,不得不让史学家们重新审视过去已有的“定论”。
来源:荆州日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canadw.com/yljj/10570.html